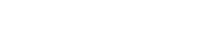文章插图
发文主题的因子结果如图所示,因子1为公共因子,在公共因子1上赋值全为负数,说明在人工智能政策发展未能体现出某一主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因子2和因子3都是特征因子,在特征因子中数值越大表现出发文主题在该因子下的特征性,场景创新在因子2上的负载值最大,可将其定义为“多领域因子” 。人工智能+X(试验区)和人工智能+X(平台)在因子3的负载值最大,可将其定义为“单领域因子” 。从发文主题的因子结果来看 , 科技部在这两个因子的负载值均为最高 , 前者为0.839,后者为0.226,说明该部门不仅参与整体发展规划,还对人工智能+X等具体领域负有相应的规范职责 , 是促进人工智能场景创新、科学化发展、打造多领域智能等政策制定的主要部门 。另外,工信部和科技部在“创新因子”中的负载值都较高,工信部“创新因子”负载值为0.340 , “人工智能+X因子”负载值为-0.425,这说明在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发展领域中,工信部和科技部可能存在职责交叉或者共商合作的情况 。
将SVD可视化处理后的二维散点图能更加清晰地聚焦发文主题和发文主体的关系 。可见,发文主体与发文主题之间并未存在强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些明显的聚类 。
2017年以来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政策的阶段性来体现不同时间切片下发文主题的重点和演变 。2017年-2018年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初始期,这一时期的发文主题较少 , 仅仅只有总体规划性和学科领域性的文件出台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作为我国第一个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系统部署的战略规划,提出了AI发展的总体思路、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同时 , “人工智能+教育”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 。2019年-2020年,发文主题和发文主体较之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增加,多部门齐头并进 , 围绕人工智能建设标准和产业规范的主题逐渐增多 。“人工智能+X”的主题涌现,新模式、新样态的《通知》层出不穷,相关部门先后两年出台针对“人工智能+试验区”的工作指引,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修订,“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主题也得以延续 。2021年-2022年这两年,发文主体开始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安全问题,在兼顾发展主题的同时也不忘管控治理,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效力层级相对较高的司法解释文件和法规制度 。但负责发展和治理主题的主体部门并未形成结构化的网络,这说明目前我国尚未将治理融入到具体的沿革路径里 , 仅仅对人工智能的设计制造和使用范围作出预先性的防范,并未在具体发展场景中介入调节和干预 。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政策工具分析
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支持,政策工具包括一系列的方法、机制和手段 , 在不同学者对政策工具的论述中 , Rothwell, Zegveld按照政策对科技活动的作用层次,将政策工具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即政府通过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手段直接供给;二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即以法规制度等策略性约束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需求型政策工具,即要求政策拉动市场需求,增加市场的活力,消除不利于政策对象市场发展的因素 。[4]在对19个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后,总结出了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工具的具体维度 。
从政策工具的条文分布来看 , 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中涵盖了三个主要的政策工具,最为主要的是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占比为56%和27% 。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以策略措施和目标规划为主,“加强、构建、调整”为关键词,对人工智能的基础层面、应用层面、技术层面进行政策性策略引导,所涉及的措施较为全面但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关注人才和财政投入,在人才投入方面,多以教育培训 , 加强人才资源保障来实现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需求 。另外在财政方面 , 政策鼓励各地试验区的创新发展并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并通过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 , 激发企业积极性和行业活力 。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来说使用较少,目前仅仅依靠宣传引导、开展公共活动来提高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水平及拉动需求 。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聚焦于推动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国际标准和伦理规范 , 补齐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短板 , 这是兼顾人工智能监管和发展需求的重要维度,但该政策工具目前使用不足 。
结论与展望
自2017年《规划》提出以来,人工智能的行业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已经初具规模,甚至小有成就,从刚开始的单一发文主体到建立发文主体间的内部合作网,有关人工智能的相关政策制定和颁布的体系已日渐成熟,主体责任日趋明晰 。政策发文主题逐渐“由模糊到聚焦”,从“整体规划”到“人工智能+X”的具体领域发展 , 再到对“科技伦理”的关注 , 人工智能的政策文本正在与现实发生密切碰撞 。为了回应AI发展的现实关切,相关的政策里也体现出了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据主导地位 , 由于人工智能涉及到的类别、模式、场景繁多,因此大部分的政策都从“政策引领,行业自律”这一块入手,给人感觉“整体有余,而细节不足” , 自主解释性较强,强制规范性较弱 。
为此,本文主要提出两大建议:首先是优化政策主体网络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多部门联合商议的产物,因此 , 我们有必要关注部门间的沟通是否畅通、是否透明;是否存在权责交叉的问题而考虑部门合并 , 节约资源;是否需要专门建立相关小组,就人工智能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另外 , 政策的效力问题也是有关部门需要考察的重点,要思考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效力层级较高的政策文本来管理和规范,以及政策效力的约束时间规定 , 以防政策成为无效的“故纸堆” 。
【ChatGPT争议不断,关于AI,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少政策】其次是完善政策工具应用结构 。供给型政策工具的直接推动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间接引导作用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是促进我国人工智产业发展的三驾马车,三者缺一不可 。[5]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的政策工具存在环境型过溢 , 而需求型不足的情况 。在生成式AI引发如此大的热议之际,我们亟需正视机器生成内容的价值和人类作为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更多样的方式来加强监管,增加合法利用AI的社会需求,减少违法使用而牟取利益的非公共需求 。另外 , 调整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维度比例,在法律规范上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稳定 。
- iPhone手机怎么设置休眠不断网
- 中西经典角色混演惹争议 罗密欧与祝英台人物介绍
- 不断的近义词是什么
- 不断学习用什么成语形容
- 含有舍的成语
-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假定生产率随时间不断增长
- 超过仲裁时效的后果
- 形容连续不断的成语介绍 形容连续不断的成语
- 表示前后相连连续不断的成语
- 五一首日订单近七千,让于虎不断称赞的明星级小车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