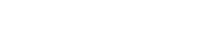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雪菜的冬天】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文章图片
□雪樱
我喜欢雪里蕻的名字,就像喜欢第一场雪的调皮与任性 。 入冬,总是脾胃、味觉、记忆抢先开启冬天模式,最后才是身体 。 舌尖对雪菜的贪恋,似乎成为我每年一次心灵迁徙的精神标记 。 雪里蕻,又名雪里红、雪菜、春不老、霜不老,像极了它的笔名,随手署在北风里、雪地里、餐桌上、菜谱中,既风雅又俏皮,给人以美的洗礼 。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供暖的前一天,城市迎来寒潮天气,清晨窗户上起了一层白霜,鼻翼上顶着一团凉意,下单叫了个早餐,看到小店新上架了雪菜肉盒,心头狂喜,遂果断点单 。 然而,肉少菜咸,败了兴致,绿汪汪的雪菜被整成了暗绿色的腌渍品,又老又咸,难以下咽 。 吃完一整天嗓子都是辣的,好像扎了根刺般不适 。 母亲说,估计是陈年腌制的,用的粗盐 。 那暗绿色的雪菜怎么能和出自母亲之手的雪菜相提并论呢?过去,每年腌制雪里蕻是我们家必做的功课 。 母亲去集市上买回一捆新鲜的雪里蕻,叶子支棱,绿得晃眼,先择后晾,用塑料绳分别绑成小把,在楼前晾衣绳上依次铺开 。 几天工夫,绿叶耷拉了脑袋,一股清冽的味道扑面而来,裹挟着自然的精华与大地的秘密 。 晒好了兴冲冲抱回家,仿佛抱着一群绿孩子,母亲搬出发面蒸馒头用的大瓷盆,在面板上用细盐一遍遍揉搓雪里蕻,压得面板吱呀呀作响,揉出了满头大汗,揉出了过冬的氛围 。 最后,把雪里蕻一层一层码进盆里,一个星期后,就能洗净食用了 。
雪菜的吃法有多种,剁碎蒸蛋羹,切丁炒肉末,还有雪菜海鲜汤、雪菜蒸大包子等 。 我最喜欢两种吃法,凉拌雪菜和雪菜炒肉 。 刚腌好的雪里蕻,带有一丁点儿呛辣味,切成小丁,剁点姜末,滴几滴香油,轻轻拌匀,就馒头吃,爽口又下饭 。 特别是以前大雪封门的日子里,市面上很少见到青菜,或是青菜贵得离谱,百姓人家吃不起,便煮一锅地瓜粥,切盘雪里蕻,眼看雪菜在热粥里缓缓舒展,那绿意直接氤氲到心底,叫人心情明媚起来 。 喝粥,配好咸菜,绝对是一件美事,比吃什么大鱼大肉还要过瘾 。 想想室外大雪纷飞,室内暖气充足,一边吸溜吸溜端碗喝粥,一边咬着透明的茎嘎吱嘎吱响,“人间送小温”的美好不过如此 。
最能令人大快朵颐的是雪菜肉丁拌面 。 提前一天买来精肉馅,干煸辣椒,炒出一大锅雪菜肉丁 。 晨起,下一锅白面条,浇上卤子,拌匀入口,越嚼越香,连吃两碗都不嫌多 。 我吃过最有故事的菜肴当数雪菜蛋花汤 。 认识一位住在干休所里的老人,他去世后,老伴独居,保姆换了好几茬,但都学会了做这道菜肴 。 后院的坛子里取出腌好的雪里蕻,清水洗去盐粒,切成小段,磕个鸡蛋打汤 。 很多时候,老太太不舍得放鸡蛋,只放雪里蕻和干辣椒,做好后端上桌,先吃米饭,再吃菜,最后喝汤,那慢条斯理的样子颇有大户人家的优雅,叫人看得眼底温热 。 偶尔,子女过来,留下吃饭,磕上两个鸡蛋,老太太就会满脸不悦,操着一口长沙方言碎碎念,隔着厨房的玻璃,两人打嘴仗,那场景也是冬日里独一份的风景,让人不禁想到汪曾祺晚年说过的,“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 ”咸菜汤与雪,就是化不开的乡愁,就是生与死的船票 。
要知道,一家人围坐吃咸菜、转着碗沿喝粥的日子是最值得珍视的 。 或许,曹雪芹最是深谙这个道理,《红楼梦》里写尽珍馐美味,比如被刘姥姥说成十只鸡搭配一只茄子的“茄鲞”,年少时看热闹,忍不住垂涎欲滴;中年时再品味,顿悟这是曹公借刘姥姥之眼看破人间富贵的真谛,至于具体怎么烹饪已不再重要 。 小说第67回,林黛玉吃饭时想念故乡,雪雁问黛玉道:“还有咱们南来的五香大头菜,拌些麻油醋可好么?”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赘了 。 ”五香大头菜是苏州人家常见的咸菜 。 吃的哪里是大头菜?分明是想家了 。 无独有偶,第75回,贾母吃饭时,王夫人端上一碟椒油莼齑酱,贾母见后笑道:“这样正好,正想吃这个 。 ”而贾赦孝敬了两样菜均被退了回去,“将那两样着人送回去,就说我吃了 。 以后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然来要 。 ”寥寥几句,颇有深意,贾母的吃与不吃、留与不留,都蕴藉着“物极必反”的生命哲学,她参透人世间的因果规律,甚至把吃饭也视作修行,她的取舍,哪怕是一碟辣酱,也关联着大观园的命运 。 就像苏东坡当年遭遇“黄州惠州儋州”,天寒地冻之时,在菜地里发现一寸冒出来的嫩绿芹菜,于是,他忆起在老家眉山母亲和妻子做过的“春鸠烩芹菜”,最朴素的食材往往最能慰藉灵魂 。 有过“举家食粥酒常赊”经历的曹雪芹,自然感同身受 。 最艰难的时候,他糊过风筝,给人代笔写过信,所以落笔的时候处处体现平等、体恤众生——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罪、饱尝过的不为人知的血和泪,都灌注成了命运的盐,成为贵族文化的精神底色 。
- “柴犬买一只可爱的不就行了?有没有血统证书无所谓”
- 大力士和健身人士的肌肉到底有没有差距?网友:差大发了!
- 心理测试:三个黄瓜,哪一个是最脆的?你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有多大
- 心理测试:哪碗面让你食欲大增?测你内心的野心有多大
- 有人喜欢到农村专门收购旧缝纫机,尽量别卖里面是有讲究的!
- 心理测试:你觉得哪个红薯最好吃,测你人生的贵人会是谁
- 心理测试:选出你最喜欢的花,测出你的智商跟你头脑的精明指数
- 衰老|“年轻”男人的“最爱”,常吃这5种食物,你也可以变得“很年轻”
- 后遗症|脑血管意外后遗症老年人的照护重点
- 让泰迪犬长寿的6个好习惯,你做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