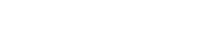界面新闻:《我们的天才儿子》受到关注后,媒体与文中“天才译者”金晓宇进行沟通,金晓宇随后以自身视角讲述的经历与父亲金性勇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完全一致。精神障碍患者们该如何褪去“被讲述者”的角色?
马燕桃:人类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寻求或者创造某种意义,但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家庭中,家庭照料者和患者本人对同样的事实感受不同,想创造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在这个事例中,父子俩10年翻译了很多本书,他们“共谋”了一件事,对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互相认同的,但具体感受可能是不同的。
我们在采集患者病史时,也经常听到患者本人讲述的故事和家庭讲述的故事有分歧。重要的分歧点在于对患者本人在社会网络架构上的表现评价。比如在这个事例中,晓宇自述:“我不适应上学、上班。”父亲称:“晓宇突然说,我不上大学了,也不要读高中了……他真的天天赖在家里。”能看出,当时的晓宇不想和社会有更多衔接,他的倾向是自我满足。
但父亲和母亲想给他安排工作。“让朋友帮忙,介绍晓宇去解放路新华书店当售货员……又把晓宇介绍到排气扇厂当工人……”在“安排”之中,我们看见了“社会”二字。“我怎么给孩子安排一个正常化、社会化的生活?”这是照料者(父、母亲)的角色。
其实看到金家房间的照片,我很有触动。他们在1988年住进了那间房子,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知道在80年代住那样房子的人,后来大部分改善了住房条件。我们按照所谓“正常化”在走,通过上班挣钱,提高物质水平。可是这个家庭的空间停止在80年代,为什么停止在80年代?其中有疾病的因素。仅从这一点,父亲的感受能不能完全被忽视?不能。他背有养家糊口的重担。
单纯地说,如果条件允许,孩子生活在个人的城堡,又有创造的才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社会化背景中,孩子出现不适应社会的情况,甚至有退谢性表现,父母遇到这样的难题,也只能从自己的身份和角度去感受,他也希望孩子自由地生活在城堡里,但现实可能非常残酷。
我们听到了父亲和孩子不同的声音,这两个不同的声音不是谁应压倒谁的关系,它们都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不管是晓宇目前冷静的表述,还是在故事里他所展现的令人似乎不可相信的突发的暴力行为;不管他父亲是在公众面前知识分子、含辛茹苦的形象,还是在儿子眼里,有时发怒的形象,这些都是真实的生活所在,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真实,我们也就不接受疾病带给我们的真实体验。
界面新闻:你怎么看待这个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故事创造了一个社会热点?
马燕桃: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是,父亲叙述了一个“疾病”和“创造性”之间的故事。在过去,精神疾病甚至被看作“残疾”,残疾有什么好说的?可是这位父亲在“残疾”里面创造了一束“光”。所有人都会希望在“我”的残缺之中,有一种创造性存在,是这束“光”触动了大家。
情绪障碍患者,我们看他不好的时候,他是得病了。但这个病里又隐含创造力。我有个病人16岁,本来也是一个学霸,在读重点高中,突然就情绪不好了。他也有非常特殊的感受,在抑郁时会拿起iPad来画画,每次来就诊,我都看到他的画。他说:“一旦你们把我治好了之后,我就不会画了。”我说:“真是对不起,我们把你治成了一个平庸的人。”
这种创造力和情绪之间的关联性,在这一群体里确实是相对突出的,这也是“天才儿子”这个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如果晓宇没有得病,他无所事事,在家待了10年,翻译了20本书,可能这个故事没人听。但一个病人,10年翻译很多本书,了不起。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社会需求,得了情绪病的人还有产能,这是多么激烈的故事。
- 心脏|知名女星抢救48小时“捡回一命”,女性务必警惕这些不典型症状
- 妇科疾病|十堰市人民医院“国医名家传承创新”系列报道⑥十堰市人民医院陈静:用综合治疗为患者解除病痛的知名中医
- 金晓宇|“天才儿子”金晓宇故事刷屏 躁狂抑郁真的多才俊?
- 精神障碍者|新闻8点见丨“天才儿子”金晓宇之外:精神障碍者的康复困境
- 晓宇|“天才”金晓宇故事刷屏,躁狂抑郁真的多才俊?
- 方面|“天才”金晓宇故事刷屏,躁狂抑郁真的多才俊?
- 李嘉欣|知名女星自曝病重进ICU,抢救48小时“捡回一命”!这种病冬季易高发,厦门女性千万要警惕这些症状!
- 从“天才儿子”金晓宇,走进躁郁症患者的“双面人生”
- 情绪|从“天才儿子”金晓宇,走进躁郁症患者的“双面人生”
- 赵赫|央视知名主持赵赫突传去世!这些“平平无奇”的生活习惯,让我们深陷癌症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