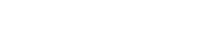值得注意的是,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银屑病患者患MAFLD的可能性比无银屑病患者高70%(比值比(OR) 1.70, 95%可信区间(CI)1.1-2.6, P = 0.01), 与MetS和其他常见AFLD危险因素无关. 在随后对同一队列的分析中, 报道了通过瞬时弹性成像检测到的晚期肝纤维化在银屑病患者中的患病率高于非银屑病患者(8.1%比3.6%, P<0.05), 银屑病患者发生晚期肝纤维化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2倍(校正或2.57, 95%CI 1.0-6.6)[115]. 同样, 在一个较小的病例对照研究中, Gisondi等人[116]报告, 银屑病患者的MAFLD纤维化评分(即一个识别晚期肝纤维化的无创评分系统)高于对照组, 银屑病预测晚期肝纤维化, 独立于MetS特征和其他潜在的混杂因素. 此外, 与以往的研究相似, 研究还发现NAFLD银屑病患者的PASI评分明显高于非MAFLD患者.
现有的数据显示, MAFLD在银屑病患者中的患病率非常高(影响了这些患者的50%), 独立于共存的MetS成分. 此外, 银屑病患者活检显示的MASH的相对晚期表明, 在这一患者群体中, 长期肝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增加[117]. 因此, 目前的证据表明, 对慢性斑块型银屑病患者MAFLD的存在应进行更仔细的监测和评估.
18.2 银屑病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潜在生物学机制
到目前为止, MAFLD与银屑病之间的联系机制还很复杂, 尚未完全了解. 然而, 确定这两种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具有临床意义, 因为它可能为新的药理学方法提供希望.
银屑病和MAFLD具有多种炎症和细胞因子介导的机制, 是一个有趣的遗传、临床和病理生理特征网络的一部分. 事实上, 可以假设MAFLD与银屑病之间的联系是多因素的(包括遗传和环境因素), 并且经常与代谢异常重叠, 代谢异常在银屑病患者中经常共存.
银屑病和MAFLD与内脏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因此很难区分MAFLD对银屑病炎症和代谢表现的个体贡献. 虽然文献中的研究不能清楚地确定MAFLD与银屑病之间的联系的方向性, 但可以想象, 有几种促炎性细胞因子(如IL-6、IL-17、IL-1、IL-2、IL-3, 局部由淋巴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分泌到银屑病患者皮肤中的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可能至少部分参与全身性胰岛素抵抗的发病机制, 胰岛素抵抗程度较高的银屑病患者是MAFLD患者. 毫无疑问, 扩张和发炎(功能失调)的内脏脂肪组织在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和MAFLD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可能通过分泌多种因素, 如非酯化脂肪酸的释放增加, 增加各种激素和促炎性脂肪细胞因子(包括TNF-α、IL-6、瘦素、内脂素和抵抗素)的产生, 减少脂联素的产生. 在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 非酯化脂肪酸流入肝脏的数量增加. 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 非酯化脂肪酸通过增加肝内氧化应激和激活炎症途径, 在直接促进肝损伤中发挥关键作用. 肝细胞因子的产生在MAFLD进展中的中心作用得到了研究的支持, 研究表明, 细胞因子可能复制与MASH相关的所有组织学特征, 包括中性粒细胞趋化性、肝细胞坏死和星状细胞活化[118,119]. 可以认为, 在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 扩张和功能失调的脂肪组织释放的非酯化游离脂肪酸增加, 也可能对银屑病的炎症性皮肤损伤产生有害影响. 然而, 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表明非酯化脂肪酸在银屑病发病中的直接致病作用.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问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迄今为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AFLD, 特别是其坏死性炎症和进行性形式(MASH), 可能加重胰岛素抵抗, 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 并释放大量促炎症、促凝血、促氧化和促纤维化介质(如C-反应蛋白、IL-6、纤维蛋白原,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 转化生长因子-β)可能在银屑病的病理生理学中发挥重要作用[118,120]. 可能通过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增加、炎症增加和各种血管粘附分子的上调而对银屑病的严重性产生不利影响. 实验还表明, 恶唑啉酮诱导的MAFLD小鼠皮肤炎症比正常小鼠更明显; 与正常小鼠相比, 恶唑啉酮激发显著增加MAFLD小鼠的耳厚、耳重、核因子-κB活性和皮肤炎症的组织学特征[121].
- 检测|山西大同报告1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 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
- 了解颅内肿瘤的相关知识
- 检测|警惕!又两省出现本土疫情,均与TA相关!多名确诊曾在同一饭店用餐→
- 国际|北京疾控:接触国际邮件14天内出现相关症状,要主动核酸检测
- 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2022年十大重点民生实事,七项与卫生健康工作相关
- 高血压|很多人的高血压,与焦虑、紧张的精神压力相关,该如何治疗?
- 幽门螺杆菌|除了胃肠道相关疾病,幽门螺旋杆菌竟还会影响皮肤疾病
- 代谢|初期大多无症状,发作起来痛“疯”!春节将至,千万别这样吃
- 代谢|初期大多无症状,发作起来痛“疯”!春节将至,千万别这样吃…
-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相关负责人到郫都区中医医院进行新春慰问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