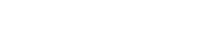新冠肺炎|由疾病而生的隐喻,如何重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文章图片
- Augusto Zambonato -
桑塔格的价值观要求一种真理:我们要看到疾病真实的面目 。不过关于疾病的真理是什么呢?桑塔格有时被指责为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她认为关于疾病的真理只能用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中那种冷静、客观的语言来讲述 。罗德关于癌症的文章是一种自白,而桑塔格拒绝从冷静客观的分析跌入个人化的自传 。(然而,女性的论作总被解读为是个人化的 。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称,《疾病的隐喻》“是一本非常个人化的书,但为了合乎体统而假装是一本论著” 。)《疾病的隐喻》可能是在她癌症康复后写的,但它绝不是一部回忆录 。正如安妮·博耶尔(Anne Boyer)在《不死者》(The Undying)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描述乳腺癌和化疗时,桑塔格从未在同一句话里同时使用“我”和“癌症”这两个词 。
【新冠肺炎|由疾病而生的隐喻,如何重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桑塔格用文本的晦涩来对抗一种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身体视作不断发号施令的权威 。生而为人,就是要发现自己是被他人解读和阐释的个体 。无论是对于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的“现充”还是紧张不安的“社恐”,社交总是一种在展示与隐藏之间来回切换的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自我的塑造取决于我们将哪些看作密不示人的隐私 。而疾病打破了这种动态 。疾病的部分作用是,扰乱从我们模式化的、天生的行为中涌现的自我感知,以及我们将这种感知投射到社会环境的能力 。在疾病中,我们对于身体的感知不再是“由内而外”可以把控的,而是由他人加工过的有关这具身体的经验(例如医生或朋友对于病状的描述),从外部接管并渗透了我们原本的感知 。博耶尔的回忆录中戏剧化地表达了这一进程 。“生命……在肿瘤学这一陌生的术语下被打破了 。”她写道:
病人变成了信息……护士会询问我关于自己身体的感受 。他们把我描述的感觉输入电脑,点击对应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长久以来被指定为某一特定的种类、名称,以及对应的保险种类……我把自己的感觉信息化了 。是医生在解读我——或更确切地说,在解读我的身体变成了什么样子 。

文章图片
- Maggie Chiang -
对于桑塔格和博耶尔来说,癌症是一种令人压抑的体验,让能够被他人解读的身体代表她们本人、甚至越过她们本人说话 。只不过对于桑塔格来说,这里的身体是通过关于癌症的道德隐喻来表达的;而对于博耶尔来说,则是通过官僚化医学中苍白的词汇 。在桑塔格的分析中,疾病的隐喻使得她对于他人来说变成是可解读的,而她也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厌恶 。
不过也有像罗德这样的病人,在疾病威胁着要吞噬他们之后,也会使用隐喻来重塑他们对身体原本的感知 。对于这样使用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应该会如何看待呢?这很难说:虽然桑塔格告诉了我们很多,要如何不去谈论疾病,但对于我们应当如何谈论疾病,她却相对少言 。有一些零散的线索:在她之后出版的著作《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她把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视为疾病写作的范例 。《瘟疫年纪事》出版于1722年,为1665年在伦敦爆发的鼠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当然,这是一部纪实小说:笛福将死亡人数列成表格,否认有虚构情节;他故意巨细靡遗地描述,但却十分引人入胜 。他的小说像是一块透明玻片,我们可以透过它看见鼠疫万人坑和紧闭的房屋,他们就在那里,不曾被解读 。桑塔格赞同这一做法,因为他没有“进一步将鼠疫理解为一种天罚或……一场巨变” 。
- 人员|速扩!江西疾控刚刚发布新冠疫情紧急风险提醒!这些人须集中隔离!
- 肺炎|遵义120教你肺炎伴胸膜炎怎么办
- 北京冬奥运动|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运动员村相关人员新冠疫苗接种率接近100%
- 领导|邵阳召开强化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管理工作视频会议
- 接种|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797.48万剂次
- 国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93763.2万剂次
- 接种|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55.82万人
- 报告|16日15时-24时,珠海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详情公布
- 防控|【北京疾控提醒您】关于本市海淀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溯源情况通报
- 经验|张文宏:今年年底可能结束新冠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