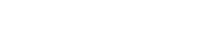新冠肺炎|由疾病而生的隐喻,如何重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三 )
文章图片
- Rebekka Dunlap -
2013年,当我第一次读到桑塔格的文章时,我患有严重的疑病症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恐惧,并持续了近十年 。我担心最多的是癌症 。我怀着近乎痴狂的心情,想象着肿瘤在我的乳房和肠道中生长 。当然,阅读桑塔格的文章并不能治愈我的疑病症,但确实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 。桑塔格关注的是,那些因为疾病被赋予过多意义而遭受痛苦的人们 。我一直都很痛苦,因为我没意识到自己对于疾病的执迷,其实是对于疾病所代表的东西的执迷 。桑塔格反对对疾病的阐释,但阐释正是我所需要的:只有当我发现疾病有意义时,我才能明白我可能并不是真的生病了 。
2020年3月,当疫情在英国蔓延时,我的疑病症又复发了 。但这一次,我并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担心自己可能会染上新冠病毒 。
对于癌症和结核病幻想的关键在于,两者从来都不是一种集体经验 。而新冠肺炎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得这种病,但我们都共同经历着这场疫情 。因此,它所带来的幻想不是个人化的(不是所谓“易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格类型”),而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且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
正如桑塔格在文章末尾所详细论述的那样,政治上对疾病的使用,通常是将内乱与疾病进行类比,或是将持不同政见者视作政治体中的“毒瘤” 。但近来对于新冠病毒的想象有所不同 。对于右翼来说,新冠病毒是一个被过度炒作的精英阴谋,是以自由之名需要与之斗争的又一股力量 。对于中立群体来说,新冠病毒让人联想到的不是内乱,而是我们都必须经历的一场集体试验,病毒也许能把我们团结到新的国家、州、城市的共同体中 。而在左派言论中,疫情导致了政治的破裂,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 。它告诉我们,我们习以为常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梦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到这种状态 。

文章图片
- Bee Grandinetti -
不过,为我们提供了应对近来新冠幻想的最佳指引的,也许是灾难片而非隐喻 。灾难电影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它提出了有关证实(vindication)的认识论问题:灾难电影的一个常见套路是,有人察觉到灾难即将来临,但当他们试图提醒别人时,别人会觉得他们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 。正如天灾一样,一场危机常常被视作一个会揭露出此前隐藏着的真相的事件:对左翼而言,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与虚伪;对中立群体而言,是不应该因为身份政治而分裂的群体团结 。新冠幻想借用了灾难电影的“证实认识论”(vindicatory epistemology):无论我以前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被疫情给证实了 。这种幻想最好斗的版本是,认为这场危机应当而且必须说服其他人,我们是正确的 。这似乎证明,世界末日也有好的一面:它至少意味着人们不再争论 。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关于证实的幻想呢?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是:抵制并揭露它们,就像桑塔格对待疾病的隐喻那样对待这些幻觉 。这种方式很可能是正确的 。但一个更艰难的解决方式回到了桑塔格身上,在面对死亡时,她最终被迫陷入自己对疾病的幻想:我也能挺过这次癌症 。生命促成了一条奇怪的规则:人们向死而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对未来注定的死亡采取某种反抗,就很难好好地生活下去,而是踟蹰于虚无主义的悲慨,或是不问前路的愚勇 。
民主政治也有着类似的结构:它需要一场永不停歇、难断胜负的争论 。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若非毅然坚守着这样一种幻想,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善辩,虽不能骗过死神,却足以弥合分歧,那么我们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很好地与人争辩 。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的论证会起作用,我们的对手将会(或至少可能)甘愿屈从于我们语言的力量 。为了忍受争论,我们需要幻想着,争论总有一天会结束 。
- 人员|速扩!江西疾控刚刚发布新冠疫情紧急风险提醒!这些人须集中隔离!
- 肺炎|遵义120教你肺炎伴胸膜炎怎么办
- 北京冬奥运动|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运动员村相关人员新冠疫苗接种率接近100%
- 领导|邵阳召开强化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管理工作视频会议
- 接种|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797.48万剂次
- 国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93763.2万剂次
- 接种|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55.82万人
- 报告|16日15时-24时,珠海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详情公布
- 防控|【北京疾控提醒您】关于本市海淀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溯源情况通报
- 经验|张文宏:今年年底可能结束新冠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