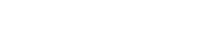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他们被骂是死者附近的兀鹫,却也是 30 万人活下来的希望】「好几次家属同意了 , 文件全部签好了 , 那边心跳一下子没了 , 器官缺血 , 不能再使用了 。 」
为了减少脑死亡后的等待时间 , 协调员需尽可能在脑死亡发生之前完成相关文件的准备和签署 。
于是 , 看上去 , 病床上人还活着 , 协调员就开始与家属谈起后事了 。
实际上 , 通常只在主治医生认为这个病人已经「病情不可逆」 , 几乎没有抢救可能的时候 , 才会将病人转介给协调员;而且 , 潜在捐献者家属签约表示愿意捐献并不会影响主治医生的全力抢救 。
有极少数的潜在捐献者在签约后居然奇迹般地扛过了死亡 , 痊愈出院了 , 按照规定 , 他们的医疗费用会被全部减免 , 这些人往往会在之后主动去登记自己的器官捐献 。
徐燕给我看了她相机里的照片——无影灯下 , 身着蓝衣的6位手术医生向白布下的捐献者鞠躬、默哀——这是每一例取器官手术前的必须程序 , 这位协调员会把她所做的每一例的送别照片拍下来发给捐献者家人 , 「留个念想吧」 。

文章图片
向器官捐献者致敬
「我们的决定是不能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一位协调员告诉我 , 曾有捐献者家属告诉他 , 正是这句话 , 坚定了他们捐献的决心 。
打开「新生」的门
符合捐献条件的人捐献的可能性有多大?好几人给我的回答是 , 「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前几年大概10几例能有一例肯跟你谈 , 现在大概会有两个人就有一个说表示可以考虑下 。
如何向悲痛的家属解释?通常 , 在这种情况下 , 男性协调员更多地依靠分析能力 , 而女性协调员更多地依靠共情和陪伴 。
「首先 , 人们很难接受亲人即将死亡的这个事实」 , 徐燕这样解释家属们的这种下意识地反应 。
「在这个时刻 , 如果去跟家人提 , 捐器官 , 救人 , 一般都不会听的 ,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广西的协调员李霞告诉我 , 「这种时候 , 我一般不提爱心 , 就是过去听她们倾诉 , 然后跟她们讲 , 人走了 , 那些器官还是好的 , 多可惜……」
「一个人很绝望的时候 , 如果前面是一堵墙 , 我们帮他们打开一扇门」 , 高晓刚这样描述他的工作 。
这位衬衫衣领总是很端正的协调员曾经是外科医生 , 现在是长海联合OPO的办公室主任 , 他觉得 , 帮助家属去思考他们未来的生活 , 也许是协调员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能找到沟通语言的一种方法 。
在高晓刚那间夹在门急诊大楼中间的OPO办公室 , 书架上的《医疗法律法规全书》、《工伤纠纷》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赔偿》在一群医学书中特别醒目 。
高的同事郝美杰向我谈起了她遇上的第一例捐献:
那家人来自农村 , 家里有两个孩子 , 一个即将读博士 , 一个博士在读 , 父亲被老家那边的无牌车撞了 , 撞他们的人很无赖 , 不给钱 , 怎么判都行就是没钱 。
他们把老人从家乡医院转来了长海 , 想继续救 , 救不回来就打算跟对方去闹 。 高老师得知此事后 , 先从家中的两位研究生入手做工作 , 给劝了下来 , 毕竟 , 那样做既触犯法律 , 也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
后来 , 基于各种法律法规 , 长海联合OPO为这家人提供了不少帮助……
协调员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被家属情绪带着走 , 「潜在捐献者家属所面对的死亡多属突发 , 家人六神无主 , 协调员有时需要部分地承担主心骨角色——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 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程序 , 帮他们出主意」 , 美杰这样说 。
- 南通爸爸辅导作业被气到脑出血!医生紧急提醒
- 一种被称为“贵族香水”的花,香味真好闻,一朵就能满屋飘香
- 天天吃蚝油,你知道蚝油是什么做成的吗?多数人都被误导,快看看
- 它被誉为“水果安眠药”,晚饭就吃它,躺下就睡着,告别睡眠障碍
- 全球最软的石头,经常被当作食物,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
- 脑梗|胆固醇“大户”被发现,医生提醒:“3物”再不丢,脑梗或会找上门
- 衰老|名医程莘农,用“银针”成就传奇人生,被世人尊称为“针灸泰斗”
- 如何避免脑梗?脑梗“祸根”已被揪出,这4种食物最好远离
- 水果|种一颗就能结几千颗果实,被称作沙漠“水果之王”,晒干了最好吃
- 尿酸|藏在身边的“降酸王”被发现,每天坚持吃2口,尿酸只降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