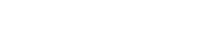这位80后的姑娘从前是移植科的护士 , 已经做了一年的协调员工作 。 见到她时 , 她正在准备与另一位同事刘菊萍搭班去协调一个案例 。 这是协调员工作的常态 , 他们通常两人一组 , 一人负责谈话 , 一人负责准备文件或负责医学护理 。
这是他们第二次面对那家人 。
几天前 , 那家的女儿因自发性脑出血入院 , 「病情不可逆 , 死亡」 , 而现在 , 那位父亲又因为工地事故摔伤 , 同样濒临死亡 。 女儿去世时 , 妈妈捐出了她的角膜 。
「孩子还没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呢 , 让别人替她去看看吧 。 」
「角膜取走后 , 医生为女孩在眼眶里装入了义眼 , 那小姑娘看上去像闭着眼睛入睡的小公主一样」 , 参加过小姑娘葬礼的刘菊萍回忆道 。
这是刘做协调员工作的第二个月 , 她喜欢拿个巴掌大小的小本子时不时跟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提得是早了还是晚了?」
很快 , 她需要去向那位妈妈谈起女孩父亲的器官捐献 , 死亡随时可能发生 , 准备文件 , 要与时间赛跑 。
在协调员的工作中 , 一家人连续遭遇亲人死亡的例子并不罕见 , 比如涉及到数个亲人的车祸 , 或是同时病倒的亲人 。
六点半 , 我眼看着刘菊萍向那位妈妈讲完她练习了无数次的结束语:「我能说的就这些 , 不管你们做什么决定 , 我们都支持 , 即使你们不准备捐献 , 也别往心里去 。 必须要跟你讲这些 , 这是我们的工作」——职业、克制 , 我们只是引导 。
晚八点 , 美杰、刘姐和一位实习生与三位伤者家属进入会谈室 , 一间空旷而亮堂的屋子 , 有几把椅子 , 并没有什么装饰 。
80分钟后 , 门打开 , 协调员和家属从会谈室里出来 。 一位家属轻声地对着美杰说 , 我们再考虑考虑 。
第二天下午三点 , 家属电话打来 , 答应捐献 。 几天后 , 那位父亲离世 , 他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使得三位患者获得了新生 。

文章图片
上海器官捐献缅怀活动 , 每一个签名都是一段故事
死和生的平衡
人类学家余成普在《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与中国实践》中写道:「器官捐赠 , 必然是一个处理生与死、自我与他者、个人与家庭、自然与文化、赠予与接收 , 甚至穷人与富人、地方与全球的问题 。 」
仁济OPO的主任陈小松分析家属在面对是否捐献的问题时的顾虑 , 他说:「最常见的一种顾虑是 , 人已经不行了 , 还要在他身上开刀 , 他会疼吗?」
蔡国玮则向我解释了她对这类顾虑的理解:「虽然从科学上来讲 , 脑死亡后其实这是没痛苦的 , 但是他们心里面觉得是有痛苦 , 他们很难割舍的其实是一种爱 , 不管是夫妻的爱 , 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 , 很难割舍……」
通常 , 家属中有医务工作者的 , 能够更好的理解死亡 , 选择进行器官捐献的概率也就比较大 。
然而 , 对医务工作者而言 , 这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知道 , 我以前在医学院受到的教育 , 就是一定要把人救回来 。 如果他是非常好的医生 , 他的目标就一定是怎么样把这个人救回来 , 他只能有这个目标 。 但现在要改变这个目标 , 告诉他 , 我们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平衡 。 」
徐燕成为协调员之后没多久就是清明 , 跟着师兄去福寿园参加悼念活动 , 一个60多岁的捐献者家属代表上台讲话 , 他的话让我不觉心头一紧 。 老人没有拿讲稿 , 只是缓缓地说:「小时候我很怕死 , 但没有人告诉我死亡是什么 , 现在我知道了 , 我所恐惧的是对死亡的害怕 。 」
- 南通爸爸辅导作业被气到脑出血!医生紧急提醒
- 一种被称为“贵族香水”的花,香味真好闻,一朵就能满屋飘香
- 天天吃蚝油,你知道蚝油是什么做成的吗?多数人都被误导,快看看
- 它被誉为“水果安眠药”,晚饭就吃它,躺下就睡着,告别睡眠障碍
- 全球最软的石头,经常被当作食物,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
- 脑梗|胆固醇“大户”被发现,医生提醒:“3物”再不丢,脑梗或会找上门
- 衰老|名医程莘农,用“银针”成就传奇人生,被世人尊称为“针灸泰斗”
- 如何避免脑梗?脑梗“祸根”已被揪出,这4种食物最好远离
- 水果|种一颗就能结几千颗果实,被称作沙漠“水果之王”,晒干了最好吃
- 尿酸|藏在身边的“降酸王”被发现,每天坚持吃2口,尿酸只降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