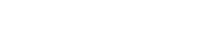舞者|癌症舞者( 二 )
陈明是绿洲艺术团最早的一批成员,刚来时,绿洲还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文艺队,成立不到半个月。
“我们当时毫无编舞能力,跳的都不算舞,只能算一种健身娱乐。”陈明戴着一副眼镜,扎着辫子,头顶冒出了很多白发。她是一位绒癌患者。
得癌症时,陈明32岁。当时医生告诉她,这种癌症的死亡率有80%。做完手术一年多,陈明也不想出去见人,呆在家里,又总是胡思乱想。她第一次来绿洲时,几个人正在跳舞,每个人笑容都很灿烂,一个工作人员问:“你看他们像癌症病人吗?”
进了艺术团,齐德明担起了编导的职责。她想把绿洲往一个专业的歌舞团上打造,拉来自己的双胞胎姐姐一起编舞,还找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教团友跳舞。慢慢地,绿洲艺术团团友们的舞技上去了,演出多了,在昆明文艺圈慢慢打出了名堂。

文章插图
11月9日,齐德明在跳舞间隙对镜整理头发。新京报采访人员王霜霜摄
团友
一支舞结束,中间休息了十多分钟。祝兰珍像只黄鹂鸟一样,在人群里飞来飞去。走到哪儿,哪里就是一片笑声。
“别人叫我们‘少奶奶’,哈哈哈……”, 祝兰珍毫无忌讳地拿自己的疾病打趣,她也是一个乳腺癌患者。
1997年,祝兰珍确诊乳腺癌。做完手术,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她掀开衣服,一条长长的竖刀疤从锁骨延至肚皮,一边的胸部凹空了。
生病前,祝兰珍是一家工厂的职工,16岁进了厂,退休前是开包装机的。她是机长,一条流水线的质量、任务量都压在她头上。自己的性格好强,每年都想争“先进机台”的称号。完不成任务,“着急啊,上火啊”。在厂里吃饭,祝兰珍没上过桌。打了饭,端着一路吃到车间,洗洗碗,继续干活。“像跳舞这些”是她从来都不感兴趣的。
切掉一个乳房两年后,祝兰珍又被推进了手术室。腋窝长了包块,10根淋巴被清除掉了9根。又过了四年,祝兰珍的子宫和卵巢一起被切除了,上面发现了肌瘤和包块。“我是个老挨刀的”,她说。
第二次手术后,祝兰珍申请了提前退休,那一年,她43岁。
刚进绿洲艺术团时,她只敢站在后排,觉得自己跳得不好。但看着跳得好的人,心里又羡慕。排练回去,她在家开着音响,开始回味,哪个动作跟哪个动作连贯,“如果卡在那一点,就走不下去”,不自觉就用手比划起来。
刚学跳舞时,祝兰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驯服自己的那个“假胸”。少了个乳房,她花400块钱买了一对硅胶义乳,用了十几年,里面的硅胶像化了的猪油。
“有二三两呢”,祝兰珍拎着装着义乳的胸罩说。她把一块布缝在胸罩里面,把义乳塞进去。有时,跳着跳着舞,两个胸就一高一低。
刚买的新胸罩,祝兰珍会重新加工一下,拿一块新布缝在胸罩里面,针脚缝得严严的,漏一个小口,这样把硅胶义乳塞进去,就不会移动。

文章插图
绿洲艺术团参加演出,第一排中间为张渝生。受访者供图
67岁的张渝生,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喜欢把发白的短发从脑门后梳到耳朵前,张渝生说自己身体素质一直很好,还是半大小伙子时,常到海埂公园一圈圈地游泳。
2006年,被查出肺癌,做化疗时,别人连喝口水都要吐,他还能在病房吃掉一大碗妻子买来的米线。
张渝生曾是艺术团最积极的团友之一。但在去年,他一度因妻子的突然离世而一蹶不振。
张渝生和妻子是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在宣传队里。张渝生会跳,会唱,嗓音高亢,宣传队里排《智取威虎山》,演员在台上演,他在旁边唱。既唱杨子荣的唱段,也唱少建波的。没有麦克风,全凭自己的嗓子把音送出去。他的肺活量高,在乐队里还吹小号。
- 国人历来重视精神对治疗疾病、养生保健的重要作用|心平气和,有益健康的“良药”
- 浴室里的“它”,可能是癌症帮凶,多数人洗澡时比较喜欢用
- 体内有癌,腰背先知晓?出现这2种标志,或是癌症“警告”?
- 癌症|年仅四十出头却确诊癌症晚期,现在他只想说……
- 经常耳鸣怎么办?别担心!这篇文章给出了5种应对办法
- 天然|15种能减少癌症发生的天然食物,日常多食用有助健康
- 全局|眼观全局耳听八方 2022年1月上
- 会吃的人最健康,推荐吃三种食物,减肥瘦身,增强抵抗力
- 运动|测一测,你的气血得几分?
- 预防|青少年如何预防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