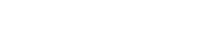文 / 草木一秋 图 / 张进路途好像越来越黑|从发病绝望崩溃到习惯共处,我经历六个阶段 || 渡过( 三 )
就在你以为自己就要好了 , 甚至偶尔能感受到美好的情绪了 , 好像一切都要达到“好”的峰值了时 , 你会突然跌入谷底:忽然的控制不住自杀自毁意念 , 让你一同经历前三个阶段加起来总和还要满的痛 , 让你生不如死 , 也让你控制不住做出更疯狂的自伤行为 。
我在抑郁的第四年下半年经历了这个阶段 。 清醒的时候 , 我会去看好多好多心理专业或者相关书籍以求自救 , 混沌发作之时 , 我自毁得疯狂而又可怕 。
那天我坐在宿舍楼后黑暗的无人角落里 , 两个小时 , 抽了两包烟打了近百个自杀救助热线 。 期间通了一个 。
我努力克制和放轻松的问候后 , 一个中年女人 , 以“少年不知愁滋味 , 为赋新愁强说愁”的口吻和我单方面输出了两分钟 , 被我沉默的中断了通话 。 接着 , 更加绝望又不死心的继续拨打各个始终处于占线中的不同求助号 。 22时54分 , 寝室门禁前六分钟 , 电话终于被接通 , 但只传来了对方的一个“喂” , 就被我挂了电话 。
我不清楚我当时怎么想的 。 是这位怕遇到说“小孩子睡一觉就没那么多事了”的大人?还是因为六分钟说不完我的痛苦?还是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打通那个电话 , 以确定自己不是被放弃了的人?
我不确定 。 我只知道 , 熬过那一天后 , 我又活到了现在 。
只是 , 我今天好像突然想明白了 , “长期不语者终失其声” 。 这么多年了 , 从十四岁到现在二十岁 , 最美好的花样年华 , 全部由它与我共同渡过 , 而在学会伪装后 , 即便再痛 , 我也始终不吭一声 , 至那一刻 , 我已失去的诉说痛苦的声音 。
但还好 ,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 我熬过了那段疼痛 。
六习惯共处
生来平庸 , 难免失望无力 。 六年多了 , 我还没走出抑郁 。
我也开始成为了三四个身边的刚加入“生病的小朋友”的入门导师 。 以过来人的身份传授她们一些经验 。 更多的是 , 我会轻轻告诉她们:
“按道理说 , 我应该要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安慰或者鼓励一下你的 。 但是我想了又想 , 我发现我好像说不出一句合适的话 , 甚至我觉得你需要的可能也不是这些 。 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 , 应该是告诉你——你永远不孤单 , 我永远都在 , 和你一起 , 和你一样 。 ”
安慰的话 , 太过轻易也太过沉重 , 尚且还在抑郁的泥潭里挣扎的我又有什么资格告诉她们应该怎么摆脱?
与她们一起倾泄痛苦说不定能让她们感受到稍微好点 , 但我生来或者说这几年中沉默的伪装 , 让我做不成善于倾诉自我疼痛的苦主 。 我只能努力让自己不坠得更深的同时 , 尽力托刚不慎跌入其间的人一把 , 再告诉她 , 她并不孤独 , 不必害怕 。
我想 , 历经漫长青春岁月 , 我和它已被相互“驯养” 。 就像是小王子和他的狐狸 。
我们之间已经有了羁绊 , 无论过程有多崎岖、多坎坷 。
我慢慢习惯了它现在多数时间的安静和偶尔狂躁时露出动物凶狠兽性 , 张开獠牙向我袭来 。 而我除了在它安静时与它平静共处外 , 也得在它发狂时也展现出自己最疯狂的一面与之以命搏命 , 虽然结局往往只是我被它的突然袭击打到头破血流、溃不成军 。
不过还好 , 幸运的是 , 我已学会与它在绝大多数时间里 , 和平共处 。
回望过去我所经历的和记录片里所表达的 , 似乎“我们”总是不被理解的 ,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被理解?
我的答案可能会很简单 。
这世间无人不苦 , 无人不痛 。 只是他人遇到的可能只是偶尔阵痛 , 而我们稍加不幸 , 遇到的是持久而绵长的痛苦 。
- 国人历来重视精神对治疗疾病、养生保健的重要作用|心平气和,有益健康的“良药”
- “这将是疫情最后一个寒冬!”张文宏深夜发声,奥密克戎迎来克星
- 经常耳鸣怎么办?别担心!这篇文章给出了5种应对办法
- 经验|张文宏:今年年底可能结束新冠大流行!
- 全局|眼观全局耳听八方 2022年1月上
- 会吃的人最健康,推荐吃三种食物,减肥瘦身,增强抵抗力
- 运动|测一测,你的气血得几分?
- 预防|青少年如何预防白发?
- 茶叶|喝一口等于“钢丝球”刮肝!卫生组织发声:停止饮用“1茶叶”,趁早扔
- 方面|紧急通知:停业!停航!停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