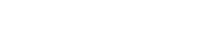相互作用|药物基于“肠-脑”通路的研究进展( 三 )
另一方面, 多数神经精神疾病治疗药物在体外显示了不同的抗菌活性 。 早期曾报道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如帕罗西汀、舍曲林和氟西汀等均具有广泛的抗菌活性, 包括对葡萄球菌、肠球菌、梭菌、假单胞菌和柠檬酸杆菌等各类菌属[44] 。 此外, SSRIs还能通过干扰细菌粘液层的生物合成来增加抗生素对各类细菌的敏感性 。 例如舍曲林可提高四环素与氟喹诺酮联用抑制解脲棒杆菌, 进而治疗尿路感染[45] 。 除了SSRIs以外,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也具有抗菌作用 。 Mandal等[46]分析了不同剂量的阿米替林对253种细菌菌株的体外抗菌活性, 其中对葡萄球菌、芽孢杆菌、霍乱弧菌的抑制率最高 。 这可能是细胞壁合成和质粒活性受到抑制的缘故[47, 48] 。 同时, 异丙嗪和丙咪嗪也被证明能通过干扰质粒复制来抑制大肠杆菌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生长[49, 50] 。 此外, 典型(第一代) 抗精神病药也对各类菌表现不同的抗菌活性 。 包括硫利哒嗪[51]、氟奋乃静[52]、三氟拉嗪[53]、丙氯拉嗪[54]和氯丙嗪[55]等 。
因此, 口服类神经精神疾病治疗药物的使用与肠道菌群组成的改变息息相关 。 众多动物模型上的研究阐明了两者具有潜在联系 。 例如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atypical antipsychotics, AAP) 奥氮平可诱导给药后3周的大鼠肠道微生物群发生特定的改变, 包括硬毛菌、放线菌, 变形杆菌和拟杆菌等多个菌门[56] 。 阿立哌唑是另一种AAP药物, 在以每天20 mg·kg-1的剂量给予大鼠4周后, 可诱导其微生物群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 包括梭菌属, 瘤胃梭菌属等各类菌的相对丰度增加[57] 。 此外, 一项探究抗抑郁药影响小鼠肠道菌群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联系 。 Iva等[58]长期给予小鼠服用5种抗抑郁药物中的任一种(氟西汀、艾司西酞普兰、文拉法辛、度洛西汀或地斯帕明) 后, 发现其肠道菌丰度有所降低, 而β多样性增加; 属水平上降低了抑郁样行为相关的瘤胃球菌属丰度, 进一步研究发现黄化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flavefaciens) 会降低度洛西汀的功效, 这为肠道菌群的抗抑郁作用提供了证据 。
临床上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了两者的关系 。 Ticinesi等[59]曾对76名老年住院患者的粪便菌群进行分析, 发现各类抗精神病药的使用均能改变患者肠道菌群的组成 。 另一项横断式设计的研究通过16S核糖体测序分析了100多名双相情感障碍服药患者和对照患者的粪便样本, 旨在研究AAP的服用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 其中所研究的AAP包含了氯氮平、奥氮平、利培酮、喹硫平、阿塞尼平、齐拉索酮、卢拉西酮、阿立哌唑、帕潘立酮和伊潘立酮等各类药物 。 结果表明, 两组女性患者的肠道菌群被显著区分, 即经AAP治疗的女性患者显示出更低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特别是Lachnospiraceae、Akkermansia和Sutterella菌科的丰度差异显著; 而男性患者则没有明显的区别[60] 。 同样, 一项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横断式队列研究中也观察到了AAP对肠道菌群的部分影响 。 尽管使用AAP的对照组患者组与未使用AAP的对照组之间没有检测到肠道菌群的显著变化, 但服用APP后患者的Alistipes菌属有所增加 。 与此同时AAP治疗组女性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也有所降低[61] 。 Bahr等[62]则更细致的调查了利培酮对肠道菌群组成的影响 。 与对照组相比, 接受利培酮治疗的儿童患者肠道微生物组发生了改变, 即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丰度有显著降低, 而这可能与患者的体重增加密切相关 。 而纵向观察研究发现在随后12个月的利培酮治疗中, 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的比例则逐步降低 。 尽管可能存在样本量小等缺陷, 但这些研究初步证明了长期使用利培酮等APP的患者肠道微生物组会产生更加独特的改变 。 在抗抑郁药方面, 一项对老年受试患者的调查研究表明, 服用抗抑郁药与肠道菌群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63]; 而另一项针对肠道菌群结构的不同群体水平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64] 。 一项针对临床290例重度抑郁症患者代谢组学的研究更是带给了人们深入的思考 。 口服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后, 体内更多地产生了吲哚和酚酸等肠道菌群相关的代谢产物; 而伴随着患者对药物效应存在高低, 肠道菌群相关的代谢物差异更为显著[65] 。
- 他汀|转告父母: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时,少吃这5物,别不放心上
- 洛神花泡茶水喝的功效 天然保健药物
- 诺华|创新心血管药物英克西兰落地博鳌乐城
- 乙醇|除了头孢类药物,吃这些药也千万别喝酒
- 抗体|国家药监局:保障新冠病毒治疗药物质量安全和生产供应
- 杨阳|创新心血管药物英克西兰落地博鳌乐城
- 双硫仑|服用这些药物千万别喝酒
- 协调员|深化药物临床发展 提升科研综合实力——我院重症医学科召开药物临床试验项目启动会
- 性疾病|【医学科普】胆固醇不高,为什么还要吃他汀类药物
- 阿奇霉素|阿奇霉素不能随便吃,建议:服用阿奇霉素时,尽量避开3种药物